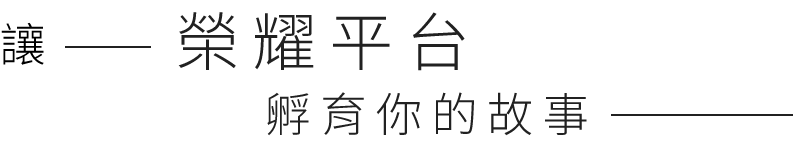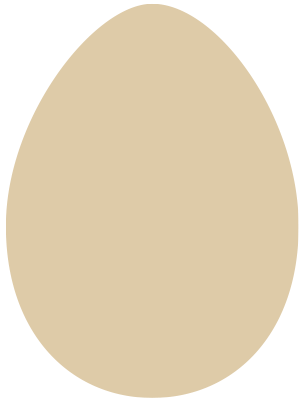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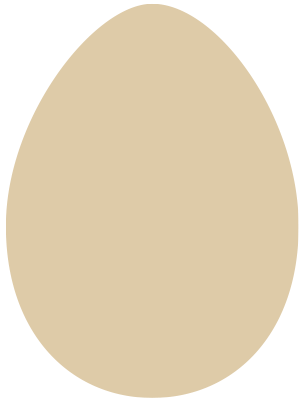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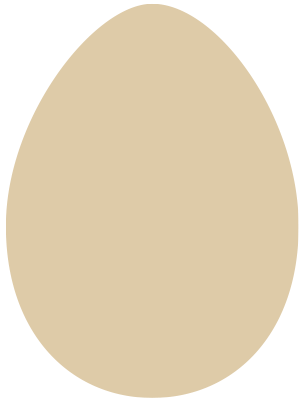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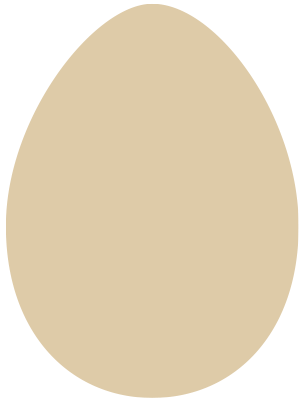
《怪胎》:一場風格為主體,故事是綠葉的瘋狂冒險
編導想要將戲做得怪怪的,但下手節制了。面對如此令人脆弱的精神疾病,我感到一種俯視的距離…這種生命處境明明可以讓人共情,可以煽情,可以狂躁又真實、怪奇又扎心,卻止於輕輕觸碰。可愛有餘,深刻不足。用力作怪,不夠有病。
文 馮勃棣(駐站評論人)
《怪胎》原作是廖明毅導演的電影,噱頭是用iPhone拍攝,其俐落與對稱的構圖、高亮度的色彩、鏡頭調度、服裝美術等元素構成強烈的視覺風格,玩了新穎的電影語言,是一部極度風格化的影像作品。當這部充滿個性的作品要改成音樂劇時,我是非常興奮的,恨不得親自操刀,投入這一場注定實驗的冒險。
會想親自操刀,更是因為電影版本有很顯著的弱點,便是劇本。在電影版本中,角色扁平沒有厚度,缺少核心衝突,最後不知如何收尾,導致突轉與爆點毫無鋪陳與根據。在這樣的故事基礎下,音樂劇是否有足夠的的素材撐起一齣十幾二十首歌的作品?無怪乎戲長確實只有八十分鐘。當然,長度不是重點,小品也能動人,只是編導應該怎麼去補足、擴充與深化劇本先天體質的不足呢?
即便劇本大有問題,我當年的觀影經驗仍是愉快的,因為我被它的影像風格給征服了。於是,此文將從「風格化的延續」與「劇本的改編優化」兩個角度來切入。
音樂劇延續了電影的風格化。故事的主角是兩位強迫症患者,該戲在畫面、調度、場上的物件、動作肢體等選擇都乾淨利落,充滿奇思同時精準果斷。整齣戲簡直就是主創團隊的強迫病徵,都是才華的火力展現。尤其是陳彥斌的編舞,狂野怪異,表現主義般地映射出主角內心的失衡失序,幾乎讓我們以強迫症的視角去看了一次世界。導演意圖明確,操作到位,才氣煥發,尤其一場描繪兩人做愛的戲,既恐慌又神經質,既殘酷又溫柔,恰如蔡依林所言,怪美的。
但在劇本面,到底是怎麼看待或利用了作為精神疾病的強迫症呢?此戲無意也沒必要去嚴謹探究強迫症,或患者究竟面對著怎樣的失活處境。這不是該戲的出發點,亦非理想的評論框架。相對的,強迫症應該是作為一個美學上的「借題發揮」,從中去延伸到更廣大的議題,關於「不一樣」、關於「怪」、關於「有病」,在這個世界中應當如何存在,進而擁有幸福的權利。
如文案所述,一片怪拼圖,並不見得就能跟另外一塊怪拼圖拼在一起。這個概念提供了故事大書特書的揮灑空間,可以浪漫、可以疼痛、可以荒謬、可以療癒,可以好笑,可以同時超怪又同時打到所有看似正常的人。
但,劇本略嫌可惜了。我只看到風格,沒有看到內裡;徒有形式上的怪誕,沒有靈魂上的瘋狂。編導很明顯刻意地作「怪」,甚至音樂也刻意不追求悅耳,形式上的風格拉到了極致,反倒讓角色像是物件棋子。電影中角色扁平的問題,在劇場中並沒有解決。

相較於電影呈現的是外部行動,音樂劇更能呈現意識中的思想、情感與辯證。在情節疲軟的狀況下,角色內心的精神狀況或成敘事主體。只是場上屢有演員與物件的流動,卻少了情感的湍流。礙於故事提供的素材與厚度不夠,使得歌詞時常隔靴搔癢。
編導想要將戲做得怪怪的,但下手節制了。面對如此令人脆弱的精神疾病,我感到一種俯視的距離。當然創作不必然要道成肉身,為其發聲更不用相濡以沫,我只是覺得可惜,角色的靈魂狀態可以更在邊緣遊走,要書寫為其所「困」,就讓人困到窒息,直到最後角色發現能和愛人一起被困,也是一種浪漫。諷刺的是當其中一人可以開門走向自由時,反倒注定了兩人的分離。這種生命處境明明可以讓人共情,可以煽情,可以狂躁又真實、怪奇又扎心,卻止於輕輕觸碰。可愛有餘,深刻不足。用力作怪,不夠有病。
回到一開始的框架,其風格化的延續保留了原作有趣的況味,但劇本的扎實度似乎被風格狠狠壓過了。是故事在服務風格,或是風格在服務故事?對我而言,本劇狀況像是強烈的風格在掩護故事的不足,以調度的華麗來彌補角色的扁平。至於歌詞是否幫上了忙?我認為太冷靜也太疏離了,身為一個愛情療傷輕喜劇,愛意可以多一點潮水,分手可以多一點眼淚。
但不可諱言,瘋戲樂依然完成了一場瘋狂的冒險。要拿電影《怪胎》來改編成音樂劇的選擇本身,就是很怪胎的行徑。這是瘋戲樂的第三齣原創音樂劇,每一齣都找到了別出心裁的議題,皆在美學上有清楚而高度的挑戰,期待他們接下來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怪的有態度、怪的有姿態,有腦有愛,有情有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