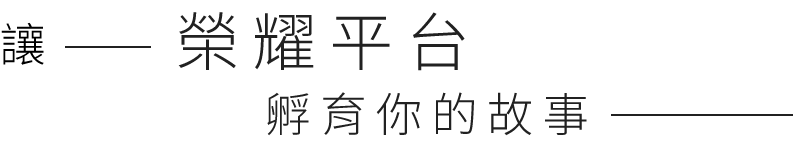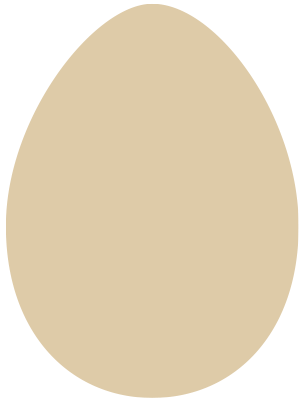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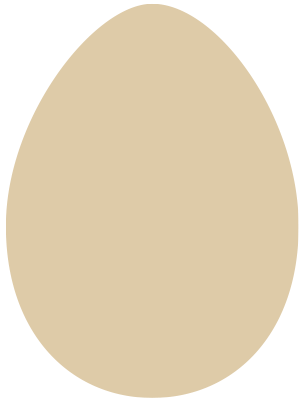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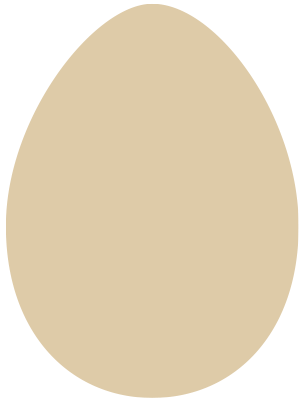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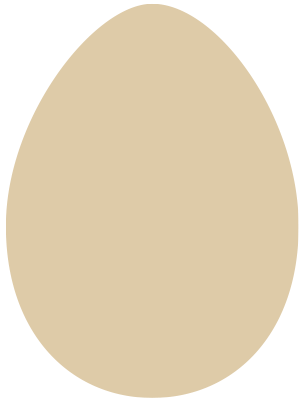
《搖滾芭比》中的三位一體:脫口秀、戲劇獨白、搖滾演唱
表演者在台上進行的是一場求生秀,加上中段有些台詞稍嫌冗長,演員必須要渾身解數才能收攏觀眾注意力以存活下來。觀眾的笑聲就是魔戒,若演員目標只剩取悅觀眾、引出笑聲,便是中了媚俗的套。全場高潮多麼迷人,但為此用力過猛,角色主體性與故事深度就消失了。如何讓這種表演質地成為角色塑造的一部分,讓演員能真誠面對文本,成為編、導、演、表演指導的當務之急,必須處理。
文 馮勃棣(駐站評論人)
《搖滾芭比》在CORNER MAX的音樂展演空間演出,演員共一男一女配上五人編制的樂隊,構成一場兩小時包含音樂演唱(奏)、脫口秀與戲劇的綜合表演,故事從東西德尚未合併說起。主人翁Hedwig是一名變裝皇后,原本是生理男性,為了愛情動了變性手術後慘遭背叛,她心懷怨恨成了搖滾歌手,在兩小時中說說唱唱,逗得全場大笑,同時侃侃而談自身境遇,帶出內心的憤怒與哀愁。
我看了兩場,中間相隔一個月,兩次觀看有截然不同的感受,主創團隊顯然不斷進行優化,我也從中抓到該型態演出的一些眉角。
飾演Hedwig的男演員必須身懷絕技,除了要會演戲,會唱之外,還要有脫口秀的本領。我將其此戲分成三個元素:脫口秀、戲劇獨白、演唱。三者構成全劇的敘事,演員必須在三種手法中穿梭自如,實屬極大挑戰。
脫口秀,更精確的說法是單口喜劇,透過表演者一人與觀眾互動,百無禁忌地胡吹亂蓋,以搏得滿堂笑聲。脫口秀多半是演員的本色演出,演繹的就是自己,至少近似自己,他與觀眾近距離搏鬥,接收觀眾最即席的笑聲、呼吸、任何臨場反應,再靈活應變出即席的回饋給觀眾。表演者與觀者的距離是近的,角色與演員本人合而為一,努力搏感情。
戲劇獨白,演員必須帶著他在故事中的身份背景、情感狀態、時空背景來敘事。演員在此進入角色,演繹台詞,帶著排練好的節奏,來呈現一個相對脫口秀封閉許多的演出。一旦演員脫離了角色,除非是設計好的後設操作,不然這個封閉敘事便中斷了。
本戲容易尷尬之處便是,到底是演員本人在講脫口秀,還是角色Hedwig在講脫口秀?第一次觀看時,演員固然魅力煥發,笑點信手拈來毫不費力,但表演者卻在「角色」與「演員本人」之間跳進跳出,形成斷裂。一下是Hedwig在進行傳統戲劇處理中的戲劇獨白,一下又回到演員本人在撩撥觀眾,導致演出被切成一段一段,無法呈現出兩小時一氣呵成的流動。在此,演唱、脫口秀、戲劇獨白三者成了粒粒分明的存在,尚未融為一體。
因此,Hedwig的整體性是模糊的,他一方面是1980年代的東德變性人,同時又有濃濃演員自身的影子。理想的狀態應當是兩者巧妙合而為一,但在前幾場的演出中,顯然主創團隊還在摸索出路。

一個月後,我又看了一個版本。主演林家麒的表現堪稱巨星。他以Hedwig的狀態講述自身故事,也以同樣的狀態處理脫口秀。在說、唱、演之間的轉換毫無隔閡,所有的銜接順理成章,以一氣呵成的流暢度完成兩小時的演出。他撩撥觀眾,該嘶吼就嘶吼,該迷幻就迷幻,該抒情就抒情,集白爛、憤世、傷感、騷味於一身。林家麒克服了一個魔戒:「媚俗」。或者說,他媚俗得很有格調。
這是一齣兩小時類似於solo的戲(這樣講對女主演有點不好意思,但我是這麼認為的),表演者在台上進行的是一場求生秀,加上中段有些台詞稍嫌冗長,演員必須要渾身解數,才能收攏觀眾注意力以存活下來。觀眾的笑聲就是魔戒,若演員目標只剩取悅觀眾、引出笑聲,便是中了媚俗的套。全場高潮多麼迷人,但為此用力過猛,角色主體性與故事深度就消失了。如何讓這種表演質地成為角色塑造的一部分,讓演員能真誠面對文本,成為編、導、演、表演指導的當務之急,必須處理。
林家麒幹得好,若要雞蛋裡挑骨頭,大概就是他演繹的變裝皇后,還是流露出滿滿的直男味。
再聊聊文本的翻譯與改編。
劇本基本上維持原時空背景設定,講述東西德時代的變性人所遭遇的壓迫。改寫的劇本中,Hedwig世界巡演,來到台灣,提及了計程車、大巨蛋等具體而真實的元素,看來只是作為搞笑素材,但認真看待之,就是失真。劇本年代又很明確提及1988年,切至2023年的今日,角色在外貌、精神上的年紀又與文本不符。我可以理解主創想要在地化與改編的企圖,只是目前點到為止的元素有點像突兀的置入性行銷,不太能融入敘事脈絡。回到前述,若作為脫口秀素材,非常合理;若回到角色與故事,則讓人出戲。
原劇中提及性別(向)、變性(裝)受到的壓迫,距離當今的台灣也確實遙遠了些,我們已對多元性別友善許多。要讓劇本與當代產生連結與共鳴,當是創作者最甜蜜的挑戰。
看完後,我深深著迷於此種三位一體的表演形式,也真的被勾起了創作魂。脫口秀當紅,但以消費和媚俗居多。我們完全可以創造出自己的《搖滾芭比》,用自己的語言,講當今的台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