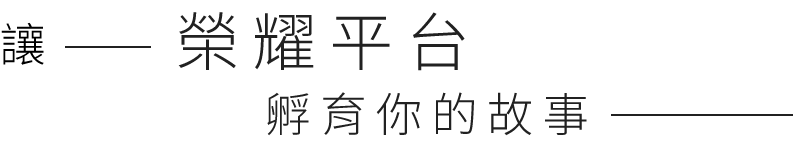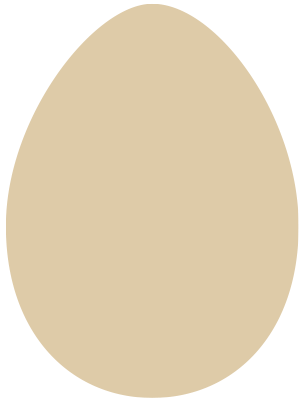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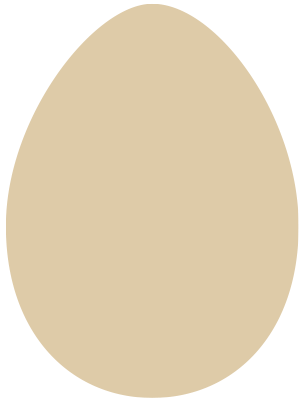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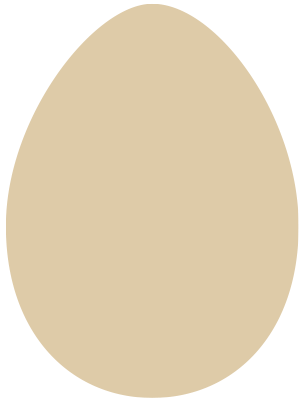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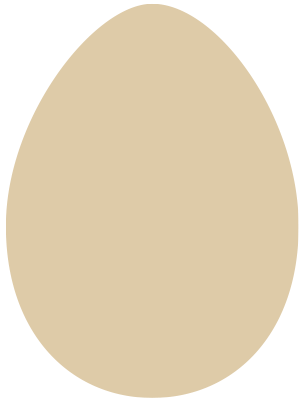
形式與語言製造的距離感:說中文的《搖滾芭比》怎麼尷尬了?
《搖滾芭比》與其說是場音樂劇,更像是Hedwig這位搖滾歌手在臺灣、在2023年的臺灣所舉辦的演唱會巡演——這種場地、表演形式等方面高度統合後所製造的極度沉浸感,反倒與劇本本身產生了距離感與邏輯的劇烈錯置。
文 吳岳霖(駐站評論人)
首演於1998年美國外百老匯的《搖滾芭比》(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),經歷多國巡演、轉譯與再創,二十餘年來不歇。在瘋戲樂工作室今(2023)年再次取得授權、並中文化之前,最近一次在臺灣演出的版本,是2018年受臺中國家歌劇院邀請來台的「韓國版」,並有韓語、英語兩個版本。相較於韓國版在標準表演藝術場館演出,這次的中文版則選擇CORNER MAX 大角落多功能展演館,其音樂展演為主的場地性質,其實更趨近《搖滾芭比》劇本內容的場景,因此完美建構一場演唱會的沉浸感受。
除場景設定於一場搖滾演唱會外,《搖滾芭比》透過演唱會常有的Talk,進一步帶出幾個更核心的背景值,包含故事時代設定於德國柏林圍牆倒後,而主角Hedwig的童年、乃至於青春期的成長則有多數時間在東德;另外則是,主角的身份「酷兒搖滾歌手」或多或少牽涉到前述的政治背景,促使他/她透過(不算是完全成功的)變性(Hedwig的生理性別為男性,而在劇中已是用女性妝扮現身),得以借用母親的護照,與美國士兵前往美國移居、結婚。因此,「性別」與「政治」成為《搖滾芭比》彼此牽涉、交疊與對照的議題,後續也將其包裝進相對通俗、八卦的情節發展。
這些複雜難解的議題在《搖滾芭比》裡確實非常明確,無論整個場景多麼像是一場演唱會,甚至時而更像是閨蜜的八卦聚會(因Hedwig講述這些事件的語氣,而造成這樣的親密感),仍會溢出這些背景值所必須帶來的深思。
不過,這次的中文版卻讓我感受到更多的是尷尬感、或斷裂感。
最初的想法是:會否「柏林圍牆倒下」以及「東、西德分裂與統一」這件事情,對於當代臺灣的我們過於無感?不過,先不論柏林圍牆拆除的1990年,以及位於歐洲的德國,與我們的距離感為何;但是,「統一」、「冷戰」等思維與影響,放在臺灣、或是放在國際局勢,縱然有諸多差異,但仍舊存在某種弔詭的感受在發酵。甚至,對於過去歷史、事件的再詮釋,本就是創作慣用的手法與材料,無論借古鑑今、古今對照,還是挖苦嘲諷。
在離開現場後,那種看完「演唱會」後的興奮感、或是惆悵感漸漸消散後,才察覺這種斷裂反而來自「當下的建立」,也就是演出現場所建構的語境,直接帶給觀看者、或是參與者的感受。

前述提及,由於演出場地本身的特性,讓《搖滾芭比》劇本內部的場景貼合了演出本身的場景,加上了演員本身帶著強烈現場感的講話內容,包含討論到場地對面的大巨蛋,經歷幾任市長的興建過程——特別是我所看的場次是由蕭東意飾演Hedwig,這種站立喜劇、脫口秀的質感則越見濃烈,也充滿隨時更新、與時俱進的效果。(暫時不歸類為前因、還是後果)這些都造成《搖滾芭比》與其說是場音樂劇,更像是Hedwig這位搖滾歌手在臺灣、在2023年的臺灣所舉辦的演唱會巡演——這種場地、表演形式等方面高度統合後所製造的極度沉浸感,反倒與劇本本身產生了距離感與邏輯的劇烈錯置。
換言之,倘若這是場巡迴演唱會,距離Hedwig開始活躍的時間點已有30年左右,揣測Hedwig的年齡,就極有可能與演員所呈現出來的年齡感完全不同——這些演員表現出來的質感都過於年輕。當然,《搖滾芭比》的人物設定本就立基於首演時間點(1998年),與柏林圍牆倒下的1990年,就可推算出Hedwig在該場演唱會的年齡;因此在巡演、重製、轉譯多年後,特別又在中文版所建構出的特質強化後,反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尷尬感。
另一方面,則是中文化造成的語言感受。此處所指的並非翻譯本身的對錯與好壞,而是當全劇的語言轉換成中文時,會出現至少兩個層面的問題,並且都建構在疏離感與親密感的拿捏。
從演員的角度來看,因為選用了個人熟悉的語言體系,增強了即興可能,但也會進一步加重「現場感」的置入;同樣地,對觀眾而言,中文本身就是在場多數觀眾的慣用語言,加上更加強烈的現場感發揮,觀眾會與當下這位演員的親密感更為親密,卻可能會與他所飾演的Hedwig——這位來自東德,變性後去美國的搖滾歌手——越來越遠。反過來說,當語言本身的熟悉度降低後,我們或許才更能確信台上這位Hedwig來自異國。
距離,製造了尷尬;或者說,此次的中文版《搖滾芭比》轉譯得過於流暢、選用的場地過於合適、演員充分發揮個人特色,反而造成了這種「不適合的距離」。不過,若要說場地合適,純粹是因為演唱會這個劇本設定,單就場地本身的舒適度,舞台與座位區的關係其實過度貼近與雍塞,觀看品質也有所影響。
很多問題可能是無解的。特別是在劇本的轉譯過程,到底需要帶給觀眾怎樣的感受,或是如何服務原始文本的企圖,都是《搖滾芭比》若要持續被轉譯,就有必要思考的。